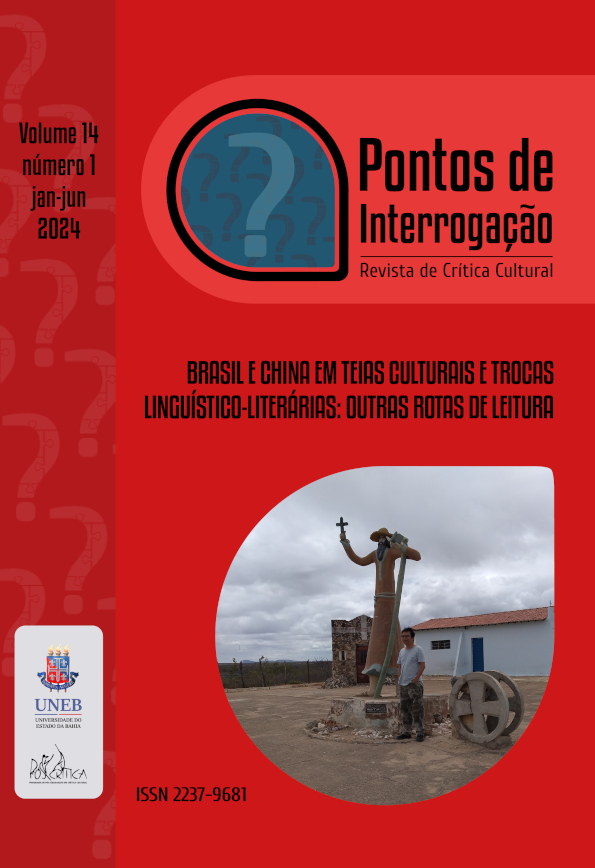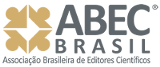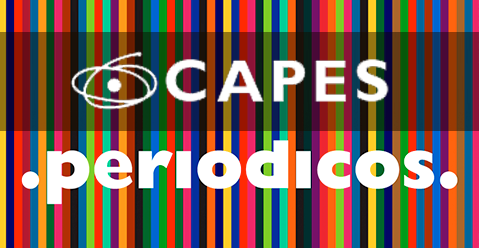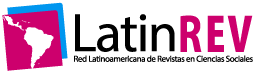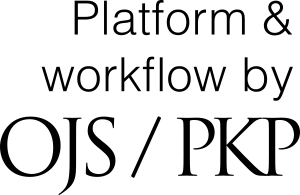Traduzir a poesia brasileira
DOI:
https://doi.org/10.30620/pdi.v14n1.p205Palabras clave:
Poesia brasileira. Tradução para o chinês. Estratégia de poeta-tradutor.Resumen
Trata-se de reflexões sobre minhas experiências como poeta e tradutor da Literatura brasileria. Destaco o processo de encontro com esta literatura, os gestos de seleção e traduzibilidade que faço nesta textuaidade. No percurso do texto, ressalto o meu desconhecimento e, em geral dos poetas contemporâneos chineses, da poesia brasileria, figurada, nesse sentido, como uma página em branco. Desfazendo essa imagem, a partir do meu encontro com a poesia brasileira, sinalizo as estratégias que criei no processo de tradução, as comparações que fiz entre a poesia brasileira e a chinesa e suas marcas também culturais, as publicações que consegui na China, destas traduções, bem como a recepção que tiveram, apontando para a necessidade de mais traduções. Entre os poetas brasileiros citados, Vinícius de Morais, Carlos Drumond de Andrade e João Cabral de Melo Neto, para este ultimo destaco minha predileção.
Descargas
Citas
Antologia da Poesia Brasileira 《巴西诗选》, tradução de Zhao Deming. Pequim: Embaixada do Brasil em Pequim, 1994. BISHOP, Elizabeth. Anthology of Twentieth Century Brazilian Poetry. Middletow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97. CABRAL DE MELO NETO, João. Antologia Poética. Rio de Janeiro: Livraria José Olympio Editora, 1978.. Museo di Tutto. Milano: Libri Scheiwiller, 1990. DRUMMOND DE ANDRADE, Carlos. O Amor Natural. Rio de Janeiro: Record, 1992. HU, Xudong. “ 若昂•卡布拉尔诗选” (Seleção de poemas de João Cabral). In: Poesia Contemporânea Internacional , v. 2. Pequim: China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 2008.. “ 若昂•卡布拉爾:詩歌工程師” (João Cabral: um engenheiro da poesia). In: Poetry , Vol. 1, n. 608, 2011, pp. 53-55.. “ 若昂•卡布拉尔诗选” (Seleção de poemas de João Cabral). In: Poetry , Vol. 1, n. 608, 2008, pp. 50-53.. “Poesia brasileira em ideogramas”, tradução de Hu Xudong. In: Poesia Sempre. Rio de Janeiro: Fundação Biblioteca Nacional, ano 15, n. 27, 2007, pp. 87-107. QUINTANA, Mário. Antologia poética de Mário Quintana , tradução de Zhao Deming e Ge Xiaocheng. Porto Alegre: EDIPUCRS. REXROTH, Kenneth. “The Poet as Translator”, In:. World outside the window: the selected essays of Kenneth Rexroth. Nova Iorque: New Directions Publishing, 1987. MORAES, Vinicius de. Soneto de Fidelidade e outros poemas. São Paulo: Ediouro, 2004. TANG, Xiaodu. “Prefácio”. In: Poesia Contemporânea Internacional , v. 2. Pequim: China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 2008. 翻译巴西诗歌 胡续冬 说起来非常汗颜,2003年我去巴西之前,对这个庞大的国家丰富 的现代诗歌资源竟然一无所知。一般人一无所知也就罢了,偏偏我那 个时候年轻气盛,因为既写诗又做一点现代诗歌研究的缘故,我总是 自诩对世界各地的现代诗歌多少都有些了解,脑子里有一幅不断被刷 新的世界现代诗歌地图。但只是到了巴西以后,我才恍然意识到,尽 管我对巴西的各个说西班牙语的邻国“出产”了哪些重量级的诗人如数家 珍、尽管我甚至可以借助一点粗浅的西班牙语阅读博尔赫斯、聂鲁 达、巴列霍、帕斯等人的少许原作,但我脑子里居然没有存下任何一个巴西诗人的名字,更别提他们的作品。 事实上,不只我一个人如此,中国当代诗人对巴西诗歌的全然陌 生是一个极其普遍的现象,这一点与中国当代诗人们阅读外国同行作 品时洋溢出来的那种引人注目的世界主义胃口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中 国的诗歌界从1970年代末期“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一直到现在,尽管有 过一些低谷,但总体上,在对待其他国家文学资源的态度上,还始终 处在巴西文学里所谓的“食人主义”时期,一波又一波诗歌译介的高潮隐 秘地塑造着中国当代诗歌惊人的创造力。一个普通的中国当代诗人, 即使他 (她)没有像我一样在大学里执教,也没有掌握足够的外语知识,他 ( 她) 头 脑 中 的 世 界 现 代 诗 歌 地 图 也 同 样 精 微 繁 复。 但 巴 西 诗 歌 对 几乎所有的中国诗人来说都是一个罕见的空白。 有时候我甚至都怀疑,就拉丁美洲的诗歌而言,500多年前的那 条因《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而诞生的“教皇子午线”是不是也存在于当 代中国的译介版图之中。这条译介上的“教皇子午线”的西班牙语美洲一侧,我们有着译著等身的译者和读者众多的译本,一些尚在人世的西 语 美 洲 大诗 人, 比如 Juan Gelman 和 José Emilio Pacheco 都 曾 来 过 中 国 参 加诗歌活动,而说葡萄牙语的巴西一侧,我们则只有可怜的一点点并 未引起诗歌界关注的零散翻译,要么出现在巴西驻华使馆自行承印的 读本上(如西班牙语译者赵德明“客串”翻译的《巴西诗选》和《马里奥 •金塔纳诗选》),要么出现在生僻的外国文学研究专业期刊之中。 大概在2004年初的时候,我在巴西利亚客座执教的生涯已经度过 了好几个月,凭着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的相似性,再加上每天的自学 ,
我已经能用葡萄牙语读点东西了。不过,因为对自己的葡语阅读能力不 是 很 自信 , 我 最 开 始 接 触 到 的 巴 西 诗 歌 , 是 Elizabeth Bishop 选 编 的 英 语、 葡 萄 牙语 双 语 版 的 Anthology of Twentieth Century Brazilian Poe – try 。这本书我主要是借助词典读葡语原文部分,如果遇到超越了我的葡 语理解能力的诗句,我再参照英译文阅读。这本书对我产生了很大的 影 响 , Manuel Bandeira , Carlos Drummond , Cecilia Meireles , Venicius de Moraes , Murilo Mendes , João Cabral de Melo Neto 等 巴 西 诗 人的 作 品 最初进入到我的视野,都是拜这本书所赐。更重要的是,这本书开启 了我翻译巴西诗歌的念头。 我 最 早 开 始 翻 译 的 是 Vinicius de Moraes 的 诗 , 主 要 是 Anthology of Twentieth Century Brazilian Poetry 里面收 选 的。 之 所 以 选 择 Vinicius de Moraes,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我觉得他的诗基本都是以情感的 强度见长的抒情诗,除了一些爆发式的夸张和率真的比喻,他的诗并 没 有 太 多 的 难 度 , 诗 句 里埋 藏 的 路 径 复 杂、 结 构 精 微 的 “秘 密 通 道”并 不多,只要把握好了他的那种膨胀、放任、充满雄性征服色彩的波希 米亚 ( Bohemian ) 抒 情 腔 调 , 翻 译 起 来 并 不 难 ; 二是 因 为 , 在 中 国 当 代诗歌自身的传统里,1980年代盛行于我的家乡四川的“莽汉主义”诗歌 和Vinicius的诗在营造不羁的抒情主体、呈现抒情的爆发力这方面略有 相似之处,“莽汉主义”诗歌在1990年代被当时注重冷峻、叙事、反讽的 中国诗歌主流所疏离,我本人也曾一度忽视它,但到我阅读Vinicius的 那段时期,至少就我个人的诗歌阅读和写作而言,我有那么一点“百无禁忌”的意思了,觉得主体膨胀的高强度抒情也并不一定会导致诗歌内 在质地垮塌。 直接导致我产生翻译Vinicius de Moraes的冲动的,是他在 《 Receita de Mulher 》 这 首诗 里的 那 句 “Que a mulher se socialize elegantemente em azul, como na República Popular Chinesa” 4 , 在 一个 中 国诗人的眼里,这一句显得非常突兀,这里面包含了极其有趣的跨文化想像,因为在今天的中国人看来,毛泽东时代身穿蓝色或者绿色军 服、 工装 服 的 女性 和 “美”这 个 概 念 没 有 任 何 关 系。 当 然 , 《 Receita de Mulher》整首诗写得气势磅礴、想象力奇谲,尽管有大男子主义塑造女性身体的性别政治错误,但我个人还是非常喜欢的。我刻意避免使用自己的写诗腔调,有意把这首诗译成了上个世纪80年代寓风流于粗犷 的“莽汉主义”腔调。2005年我回国后,曾经多次在诗歌朗诵会上诵读这 首诗的中译本,听众的现场反应都相当不错。读过我我翻译的Vinicius 的中国年轻读者们还比较喜欢引用《Soneto de Fidelidade》 4 Vinicius De Moraes, Soneto de Fidelidade e outros poemas. São Paulo: Ediouro, 2004, p. 53.
里面的 结 句 “Que não seja imortal, posto que é chama/ Mas que seja Infinito enquanto dure.” , 据 说 一些 大学 生在 这 句 对 “忠 贞”的 理 解 和 东 方传统观念大相径庭的诗句里找到了他(她)们及时和恋人分手的崇高理由。 在我2005年离开巴西之前,除了Vinicius之外,我已经零零星星翻 译 了 一些 Manuel Bandeira 、 Carlos Drummond, 、 Mário Quintana 、 Paulo Leminski 、 Ana Cristal César 的 诗。 但 我 不 久 之 后 就 锁 定 了 一个 我 的 主 要 翻 译 目标 , 那 就 是 巴 西 现 代 主 义 诗 歌 的 集 大成 者 João Cabral de Melo Neto 。 与 João Cabral 的 “相 遇”对 我 而言是 不 啻 是 一个 巨 大的 惊 喜。 我 个 人的 诗 歌 阅 读 趣 味 比较 广泛 , 像 Garcia Lorca 、 Jacque Prevert 那 样 “简 单”的 诗 我 很 喜 欢 , 像 Frank O’hara 、 Nicanor Parra 那 样 “即 兴”的 诗 我 也 很感兴趣,但最能激起我的阅读兴奋感的,还是那些充分展示了语言内部的复杂性和游戏性、善于通过精湛冷静的诗句呈现与现实世界相 对称的高度智性化的内心世界的诗人,他们的诗歌既有形式上的欢 愉、语义上的曲折幽微,更有一种使得现代诗之所以耐人寻味的集现 实洞察力、语言表现力、无边想象力为一体的综合性创造力。在我看 来,João Cabral就属于这一类诗人。 在我已经可以抛开英译本、借助字典慢吞吞地阅读葡语原文诗歌 之 后 , 我 读 的 第 一本 葡 语 诗 集 就 是 João Cabral 的 《 O Engenheiro 》。 我 被 他 冷 峻、 剔 透、 精 确、 执 拗、 充 满 了 “原 诗”( Meta-poesia ) 气息 却 又浸渍着鲜活的现实经验(特别是巴西东北部的独特记忆)的风格所 吸引,他的诗句像轻盈的海绵一样,从外到内遍布通风的孔洞,而一经阅读,这些修辞的孔洞里就会吸满份量惊人的可能性的海水(agua de possibilidade )。 我 在 巴 西 利 亚 大学 的 几个 学 生知 道 我 对 João Cabral 感兴趣,借给我好几本他的诗集,印象中,有一本选集借到我手上时 已经被翻烂了,必须拿胶水粘起来才勉强看起来像一本书。借我这本 “破 书”的 学 生说 , 他 爷 爷、 他 爸 爸 和 他 本 人都 喜 欢 João Cabral , 所 以 一家三代就把那本书翻成那样了。我从巴西回国的行囊里,还有一张João Cabral本人朗诵他自己诗歌的CD,听他本人朗诵对于理解原作的节 奏、语气、起承转合有意想不到的帮助。 2008 年 前 后 , 我 开 始 集 中 翻 译 了 30 多 首João Cabral 的 诗。 之 所 以 集中翻译他的诗,一是因为我个人喜欢,二是因为我觉得他的诗歌里可能会有很多因素值得当时的中国诗歌写作界借鉴。中国当代诗歌自1990年代起开始检讨1980年代诗歌中过于浓重的主观色彩和过于空泛 的抒情,占据“话语权”的诗人大多提倡在诗歌中引入具体、可感的叙事 性成分,来矫正诗歌中的声音与现实语境的关系。这种趋向虽然有助 于建构一种虚构与似是而非的现实多层次嵌套的复杂现代感,但持续 10
多年下来,很多新一代的诗人们在学习1990年代诗歌的时候往往不得 要领,把策略性的叙事变成了纯客观的叙事,现代诗歌中包含的创造 性 被 过 多 地 限 制 了 起 来。 我 觉 得 João Cabral 的 诗 歌 提 供 了 另 外 一条 更 为 智性化的“反抒情”的道路:在摈除诗歌表层情感的前提下,以冷静、严 谨的姿态在语言内部进行元语言的探索和新形式的实验,让诗歌写作 成为操纵着具有复杂的动力装置的诗歌机器,最终在诗歌中重新建立起“o mundo justo,/mundo que nenhum véu encobre” 5 。 坦 白地 说 , 比起 Vinicius de Moraes 来 , 翻 译 João Cabral 的 工作 非常艰难。在对待诗歌翻译的态度上,我一直相信“诗人译诗”(英语里叫 poet as translator ) 要 优 于 任 何 专 业 的 译 者 译 诗 , 我 认 为 Robert Frost 的 那 个 说 法 ( Poetry is what gets lost In translation ) 通 过 “诗 人译 诗”可 以 得 到 补救,作为译者的诗人可以用译入语言中相应的诗歌花饰替代原文中 与 译 入语 无法 兼 容 的 形 式 机 巧。 但 在 翻 译 João Cabral 的 时 候 , 我 发 现 他诗歌之中埋藏的仅在葡萄牙语中有效的小机关实在是太密集了,想 要用当代汉语诗歌的书写规则“转写”一篇包含如此多的形式“诡计”的诗 难度非常大,有时候我不得不放弃在汉语中重设那些形式“诡计”的做法 ,改为在直接译出表层语义的基础上,通过语气、修辞的变化强化它 的表达效果,暗示它在原文中的曲折感。比方说,他看起来非常简 单、 甚 至有 些 Joan Miró 绘 画 中 的 孩 子气那 首Tecendo a Manhã , 就 含 有 很多的在汉语中无法复现的小机关,特别是第二诗节: E se encorpando em tela, entre todos, se erguendo tenda, onde entrem todos, se entretendendo para todos, no toldo (a manhã) que plana livre de armação. A manhã, toldo de um tecido tão aéreo que, tecido, se eleva por si: luz balão. 6 从 se encorpando 到 se erguendo 再 到 se entretendendo 的 变 化 , 从 tela 到 tenda 再 到 toldo 的 递 进 , 最 后 两 行里两 个 词 性 大不 相 同 的 teci – do , 这 些 都 难 以 在 汉 语 里复 现。 尤 其 是 entretendendo 这 个 João Cabral 自己发 明 出 来 的 词 , 它 所 包 含 的 在 entre 、 entender 、 tender 、 tenda 之 间 漂 移 的 意 义完全无法找到相应的汉语表达。我本想把它翻译出当代诗人张枣那 种小词与小词之间互相啮合、互相激发的效果出来,但最后无6 João Cabral de Melo Neto, Antologia Poética , p. 17, Rio de Janeiro: Livraria José Olympio Editora, 1978. 5 João Cabral de Melo Neto, Antologia Poética , p. 195, Rio de Janeiro: Livraria José Olympio Editora, 1978.
能为力,只能按2000年前后汉语诗歌里最普通的“冷处理”语调译出最表 层的语意来。 2008年,中国诗歌圈比较权威的杂志《当代国际诗坛》做了一个 我 翻 译 的 João Cabral 的 小专 题 , 除 了 我 翻 译 的 诗 , 还 配 了 一篇 我 写 的 介 绍他的文章。这期杂志出来以后,在诗歌界收到了不小的反响,和João Cabral 一样 获 得 过 Neustadt International Prize for Literature 的 中 国 当 代最重要的诗人之一多多激动得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已经很多年没有 读到过这么“有份量”的外国诗歌了,中国当代重要的诗歌批评家唐晓渡 也 在 他 的 文章 中 讨 论 了 João Cabral 的 Os Vazios do Homem 里面的 “空”对 中国当代诗歌的启发 7 ,而另一位重要的诗歌批评家敬文东则在他的一篇 文章 里引 用并 讨 论 了 João Cabral 《 A Literatura como Turismo 》 里面的 那句“não nos dão seus municípios /mas outras nacionalidades” 8 。 此 后 , 中 国 官 方文化 体 制 内 “级 别”最 高的 诗 歌 刊 物 《诗 刊》 也 于 2011 年 刊 发 了 一组 我 翻 译 的 João Cabral , 并 邀 我 撰 写 了 一篇分析João Cabral诗歌特征的文章。 2011 年 , 我 对 Carlos Drummond 死 后 出 版 的 《 O Amor Natural 》 发 生了 浓 厚 的 兴 趣。 之 前 我 曾 经 翻 译 过 一些 Carlos Drummond 的 诗 , 觉 得 他的诗既能被普通读者所接受,也能被训练有素的诗人们所肯定,但 因为精力有限,没有展开对他的集中翻译。很偶然的机会,我在网上 读 到 了 电 子版 《 O Amor Natural 》 的 全 部 诗 歌 , 我 对 一个 耄 耋 老人能 够 以如此富有想象力的语言来处理最直接的性爱话题感到很意外。中国 诗歌缺乏色情诗的传统,这大概和东亚文化对性爱遮遮掩掩有一定的 关系。近些年来,也有一些流派和个人有过“泛色情诗写作”的经典案例 ,但那些“泛色情诗”都是假借性爱主题与身体语言来关注其他问题。比如 10 多 年 前 有 个 青 年 诗 人的 流 派 叫 “下 半 身写 作”, 他 们 写 了 很 多 与 性 有关的东西,但他们的焦点并不在性爱本身,而在通过书写性爱实现 对文学秩序的反叛。也有一些顶尖的诗人,成功地把敏感的历史和现 实政治问题放置到色情诗的框架中来处理。但几乎没有任何中国当代 诗人能够直接面对性爱,把性能量本身不仅仅当作激情,更当作一种 创 造 性 的 诗 歌 话 语 资 源 来 加 以 利 用。 我 翻 译 了 《 O Amor Natural 》 里面一半的诗,张贴到了“文艺青年”最集中的一个网络社区里,结果收到了 极 好 的 反 馈 , 很 多 读 者 给 我 写 信 , 说 读 了 Carlos Drummond 的 这 些 诗 , 既改变了他们“性爱不可言说”的陈见,又改变了他们对诗歌的认识——诗 居 然 可 以 这 么 有 趣! 但 我 对 《 O Amor Natural 》 的 传 播 也 仅 仅 到 网络 为止8 João Cabral de Melo Neto, Museo di Tutto , p. 56, Milano: Libri Scheiwiller, 1990. 7 Tang Xiaodu, ”Preface”, Comtemporary International Poetry , Vol. 2 nd , Beijing: China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 2008.
了,我曾试图联系一家专门出版小众文学读物的出版社将这本诗集的 中译本正式出版出来,但尽管编辑本人很喜欢这些诗,她也不得不无奈 地 告 诉 我 , 中 国 目前 现 有 的 出 版 规 定 是 不 允 许 《 O Amor Natural 》 正 式出版的。不过,倒是有另一家出版社主动联系我,他们从Carlos Drummond 这 批 色情 诗 里看 到 了 他 精 湛 而又 没 有 远 离 普 通 读 者 的 诗 艺 , 因此邀请我翻译他的《O Amor Natural》之外的诗歌用以正式出版。 有 一件 很 有 意 思 的 事 情 , 就 是 中 国 读 者 对 以 Horaldo de Campos 和 Augusto de Campos 为 代 表 的 Concretistas 的 态 度。 我 曾 经 在 我 的 “现 代 主 义 以 来 的 世 界 诗 歌”课 堂 上 讲 过 巴 西 的 Concretismo , 也 曾 在 一些 杂 志 上 撰文介绍过Concretismo和Neo-concretismo,但我发现中国诗人们(无论 是 学 校 里的 青 年 诗 人还 是 学 校 外 的 成 名 诗 人们) 对 Concretismo 几乎 毫无兴趣。这倒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中国当代诗歌尽管极富创新精 神 , 但 却 很 少 涉 足具 体 诗 ( poesia concreta )、 视 觉 诗、 声 音诗 等 实 验 性的领域。我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中文本身就 是象形文字,具有强烈的视觉指向,所以中国诗人们并不像西方同行们那样热衷于通过改变文字的物理属性来获得视觉效果;二是中国从 古至今对“诗”这一门类的界定都很严格,尽管在当代中国,诗曾经一度 以富于自我革新精神而自居,但还是始终存在这一条很微妙的边界 ——似乎大家都有一个不成文的共识,像具体诗、视觉诗、声音诗、 多媒体诗这类的作品,已经早就跨过了诗的边界,进入当代艺术(Arte Contemporanea)的领域了,而在当代中国,当代诗和当代艺术之间只 有 一些 零 星 的 跨 界 ( cross over ) 尝 试 , 大多 数 时 候 基 本 井 水不 犯 河 水。 所 以 我 所 介 绍 的 巴 西 Concretismo 、 Neo-concretismo 和 Poesia Visual 只有两类读者有一点兴趣:一是大学里学习计算机的geek们,二是个别 当代艺术家。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的葡萄牙语水平其实非常有限,它限制了我 更 深 入、 更 大量 地 翻 译 巴 西 诗 歌。 我 虽 然 不 相 信 Poetry is what gets lost In translation,但我也不是特别认同与原文差别很大的tra – -creação,我始终坚信即使是“诗人译诗”,最好也还是要从原文译过来 , 不 要 通 过 英 语 等 其 他 语 言转 译 ( Ezra Pound 不 懂 中 文却 “翻 译”唐 诗 的 案 例 , 在 我 看 来 只 能 算 是 他 的 创 作 , 和 翻 译 没 有 太 大的 关 系) , 如 果 有一天我的葡语水平能得到迅速的提升,我肯定会翻译更多的巴西诗 歌。不过我相信,即使有那么一天,我也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专业译 者,因为从前面的叙述中你可以感觉到,我做翻译大多数时候是为自己的诗歌写作服务的,我翻译诗歌的活跃期,一般都是我自己诗歌写 作的瓶颈期,在写不出诗又不愿离开诗的时候,做点诗歌翻译是最好 的 选 择 , 正 如 美 国 诗 人、 翻 译 家 Kenneth Rexroth 在 《 The Poet as Translator》中所说:
Translation, however, can provide us with poetic exercise on the highest level. It is the best way to keep your tools sharp until the great job, the great moment, comes along. More important, it is an exercise of sympathy on the highest level. The writer who can project himself Into the exultation of another learns more than the craft of words. He learns the stuff of poetry. It is not just his prosody he keeps alert, it is his heart. The imagination must evoke, not just a vanished detail of experience, but the fullness of another human being 9. (翻译能给我们提供一种高层次的诗艺操练。翻译是在伟大的劳 作、伟大的时刻到来之前,让我们的诗歌工具永葆锐利的最佳方式。 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高层次的同情心操练。一个能够将自己投射到 别人的狂喜之中去的作家,会在词语的手艺之外学到更多的东西。他 学到了诗歌的内质。它不仅仅是他一直高度重视的韵律学,而是他的 心智。在翻译中,想象力一定会唤醒的,不仅只是一段消逝了的经验 的细节,而是另一个人类个体的丰满度。) 9 Kenneth Rexroth, “The Poet as Translator”, World outside the window: the selected essays of Kenneth Rexroth, p. 171,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Publishing, 1987.
Publicado
Cómo citar
Número
Sección
Licencia
Derechos de autor 2024 Pontos de Interrogação – Revista de Crítica Cultural

Esta obra está bajo una licencia internacional Creative Commons Atribución-CompartirIgual 4.0.
Autores que publicam nesta revista concordam com o seguinte termo de compromisso:
Assumindo a criação original do texto proposto, declaro conceder à Pontos de Interrogação o direito de primeira publicação, licenciando-o sob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License, e permitindo sua reprodução em indexadores de conteúdo, bibliotecas virtuais e similares. Em contrapartida, disponho de autorização da revista para assumir contratos adicionais para distribuição não-exclusiva da versão do trabalho publicada, bem como permissão para publicar e distribuí-lo em repositórios ou páginas pessoais após o processo editorial, aumentando, com isso, seu impacto e citação.